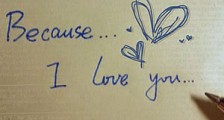香港运动:近距离观察补记——“I protest, therefore I am”!
作者:Chairman Rabbit
来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昨天笔者在香港,近距离观察了128游行《香港一线近距离观察:游行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为写到深夜,有些内容没有覆盖,今天再做一些补记。
1、昨天已经写到过。这里希望再重复一下:大型集会、散步是很多香港人寻找自我价值,寻找自我存在,自我陶醉、自我麻痹、自我解脱、自我升华的一个集体的仪式性活动。一言蔽之,就是“我抗争,故我在”(I protest,therefore I am)。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条,它背后有非常强大的心理支撑(参见笔者写的“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他们会为能够组织与参与这种活动感到由衷地自我满足和自我陶醉,是他们认为他们制度的根本优越性,也是香港人本身的根本优越性(作为高等华人的代表,似乎有与生俱来、流淌在血液中的自由民主)。这种优越感可以让他们暂时忘掉生活的艰难,经济前途的不确定性,香港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的下降,等等。今时今日的台湾,正活在这样的政治满足中。
2、实际上香港市民“政治化”已经有很多年了,每年定期都会出来搞几次游行,但这次反修例运动以来和以前是不同的:
1)本地族群意识、族群认同又有了进一步的、更加系统化的提升,现在运动有了基本固化的颜色、旗帜、口号、歌曲、文宣套路,运动生成了不同的细分阵营、职能、角色,本土派和激进主义从青年人群外扩到更大的市民群体;
2)激进意识表面化。一些先前本来就有激进想法但受到压抑的人群,开始将政见表面化。比如说从来不敢出来表达疑似港独或脱中口号的人群,现在发现终于敢随大流,公开表达自己一贯隐藏的想法了(这个比喻类似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在之前很多人内心反犹,但不会公开表达,甚至还会交一些犹太朋友,或者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交往。但到社会经历了一定的分水岭后,排犹已经成为主流,在政治上、社会上、伦理上变得可以被接受,甚至被鼓励,则大量的人群会“现形”,一夜之间变成排犹者。)香港在经历这个一个本土意识觉醒、表面化、公开化的过程;
3)当持续运动的参与人群达到一定的临界点,从边缘少数变成了主流,这时,运动带来的“社会价值”就提升了,换言之,参与这种运动可能可以帮助你建立、巩固、加深与原有社会群体的关系,是具有一定的社交功能。在特定的年龄群体或职业群体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年轻人;譬如教师、媒体、宗教界、专业人士/小知识分子等“泛黄”行业。参与政治活动有多重价值,譬如它是“政治正确”;它是巨大的同伴压力的产物;它可以帮助你交到圈子以内及以外更多的朋友。
显而易见,这种政治参与能够提供非常强的社会功能。我们看西方世界,能够为广泛人群提供大规模社交功能的往往是:
a宗教活动,例如去教堂,是为了社区保持联系;
b集体观赏型体育(spectator sports),在欧洲国家就是足球。
这时,频度就变得非常重要,一年若干次的大型活动是不足够的,人们在日渐发现其社会功能价值后,就会不断要求进行这种活动。
3、所以,中产/温和派/泛民会参加和理非活动,就是游行和集会,通过这种活动获得正能量,加深与社区/社群的联系,寻找集体归宿感,建立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排解和宣泄心理上的压抑和不满,而年轻人则通过更加激进的方式,例如统一黑衣着装的类军事组织的勇武活动。游行、抗议、暴力成了香港社会的大型社交活动。非常有意思的是,它表现出来的是社会生活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social life),同时又是政治的社会生活化(socialization of political life),即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高度融合和统一。笔者以为这就反应了香港市民的极度压抑,充满对生活的困惑,对前景的忧虑,处在认同危机(笔者更早时期撰文《香港人正在拯救自己毁掉的三观》),同时每日生活居住在蜗居里,非常需要排解、宣泄这些情绪,而又缺乏很好的疏导管道(例如足球等群体观赏体育),因此只能诉诸政治。如物质生活压力如此之大,几乎将市民扭曲至病态的香港,如果没有瞬间内爆(所有人都患神经病疯掉),那么造就出这样在外界看来难以理解的市民群体,也很正常。这是这个城市长期以降制度及资源分配对其市民心理的必然产物。
4、 12-8下午,笔者近距离观摩了游行。笔者没有和游行者产生直接互动,但也耐心聆听了市民及黑衣年轻人(主要都在路边、天桥)对游行的点评和讨论,籍此尝试了解他们的心理。随后,笔者从金钟随游行队伍一路向西走到游行终点处,并在警方布阵处进行了进一步观摩(整个观摩前后跨时6个小时)。“和理非”游行的终点是遮达道与毕达街的交界路口,民阵在此以广播车为基础,设了一个据点,宣布此处为游行终点,建议市民在此散去。大部分市民在抵达这个点或在更早的时候,就朝各个方向散去离场。但在进一步往前走,就是德辅道中,进入了黑衣年轻人的“勇武”地盘。这里基本清一色黑衣人,没有和理非。警方在租庇利街与德辅道路口布阵,不允许黑衣人再往前走。黑衣人占据了大概200米的空间。
5、笔者数次考察了警察(HKP)驻扎阵地,包括观摩HKP身后的水炮车。其中,为稍作休息,在租庇利街的金华烧腊大王吃了招牌烧味饭,喝了一碗例汤,然后出来继续观摩。警察阵地的气氛非常紧张。有大量和媒体的市民围观。这里,市民指略有年纪的中老年人,而不是黑小将。其中,一直有市民持续对HKP进行指骂。大概听五分钟就可以听到关于本次运动所有针对HKP的指控及阴谋论。另外也有市民近距离与HKP理论。笔者观摩时期,黑小将阵营(大概隔100米)一直用激光笔照HKP。HKP给过若干次警告,其中还曾拔出催泪枪做发射状。HKP一举枪,有剑拔弩张之势,空气立即非常紧张,记者让大家后退。同时,HKP立即遭到所有围观市民的高声指骂,骂他们是“黑警”、“狗”、“共产党”,不断强调“你哋已经冇着民心喇!”也用各种最难听的话辱骂HKP。北京和内地对HKP的援助是客观上加大了本地黄营市民对HKP的不满和仇恨的。当时现场观感,HKP在游行的场景里,是绝对的少数派,面临很大的心理压力。但他们似乎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另外,笔者观摩到,HKP在个别据点(如雪厂街与干诺道中的交界)驻扎(就是站着)超过六个小时,确实十分辛苦。
6、笔者也考察了黑小将大概两百米跨度的布局。这些黑小将并不完全是勇武,很多只是穿着全身黑衣带黑口罩而已。处在阵地前方和两翼有许多勇武。笔者观察到的情况:
1)人非常、非常之多,且不断还有从东边补充过来的人流。在中环这边集会的同时,他们还有很多人在铜锣湾、金钟聚集,可见人群之广,有生力量之强。笔者认为他们不是少数,就是香港的年轻人;
2)有男有女,女性比例相当的高。这说明这绝对不是一个用雄性荷尔蒙可以解释的问题,而是一个年龄群体的问题。在这个年龄段里,不分男女的香港人都会参与到运动中来。女性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主要是后勤、掩护等,并能够给男性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和鼓舞。
3) Full gear的人很多(只是在过去一两个月来,他们发现头盔用处不大,用头盔的少了),有很好的防毒面具,还有各种雨衣和雨伞装备。Full gear并不集中在最前方,往后走很远都可以看到大量这样的黑衣人。
4)组织者穿插在延绵数百米的阵地中。他们用喇叭进行组织。例如呼吁没有装备的人不要向前走;对阵型阵地做一些组织和安排。
5) 12·8是一个和理非活动,黑衣人没有设置太多路障堵路,显然没有僵持的打算,今晚就是聚一聚,主角让给和理非。
6)他们谈吐和状态都非常轻松和愉快,没有任何紧张,处在一个愉悦的气氛,好像是出来party的,是一个大型社交场所。大概这就是香港年轻人的夜店。
7)有市民在路的两边穿插。笔者也混迹其中。总体感觉是,黑衣人和市民是在一起的,黑衣人的阵地没有紧张气氛,当地人也不惧怕黑衣人。相反,HKP的阵地给人带来紧张感。如果说笔者有什么印象的话,还是他们的人数之众。这是一股巨大的、充满自信的有生力量,他们只是有意识地选择今晚不采取任何行动而已。但可以看出,他们不认为自己面临任何法律和道义的约束。
8)昨有人担心笔者的安全。笔者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自我感觉与他们交流无碍,所以多次前往并驻足观摩。因为本质是,黑小将并不针对他们眼中的“市民”——他们真心地认为市民大部分都是支持他们的。而“市民”也是有默契的,蓝丝这时根本不会在这个区域出现,出现的都是黄丝或者“懂事”的蓝丝。
除此之外,要点如下:
a)最好戴口罩出行,如果穿黑衣最好;
b)千万不要拍照或玩弄手机,非常危险;
c)避免与他们目光对视或停留太久;
d)内地人的话,也不要携带证件(包括内地的信用卡);
e)广东话不好的建议不要前往(只会说英语也不行,还是有些危险),万一有互动,被发现或疑为是内地的,容易被认为是卧底,很难解释清楚。这时跑都跑不了,马上私了。
基于这些原则,本地市民是可以跟他们相安无事,而且不觉得他们是有威胁的,反而会憎恨具有一定“不确定性”的HKP。
7、笔者和自己的爱人也住过40多平方米的蜗居。两个人。当时的感觉是,周末在家里是待不下去的。太憋屈,总想出去透透气,找购物中心、找咖啡厅,找朋友,各种能呆的地方——反正别在家里憋着就好。再看看北京的胡同。为什么大爷大妈们喜欢在路边坐着?小朋友在胡同里乱跑?因为在大杂院里,居住的空间太少,根本无从落脚。然后推开门就是院子,就是街,就是公共场所。胡同就是他们的大厅,是他们白天进行社会交往,找到社会存在的场景。家里(十几平米,几十平米的地方)只是用来睡觉的。
上面这些比喻,我相信很多人能切身体验,这就是香港的现状。人均居住面积十几平方米,压抑至极,在家里是待不下去的。一有机会,他们就希望出来走走,找找朋友,呼吸一下开放的空气。而在这个寸土寸金,消费代价高昂的地方,哪能找到什么地方?只有街头。香港运动让他们发现了街头。美国的青年可能选择home party和clubbing,欧洲的青年选择足球,香港的青年选择在街头参与政治,这是他们摆脱压抑生活的有限选择之一。尤其是,这次运动以来,无数青年与他们的父母一辈因政见不同吵翻,称自己的父母为“废老”(the answer to“废青”)。在狭小的蜗居里,他们无法面对这些对自己无法提供一丝帮助的父母——不能解决就业,也不能解决住房和婚姻。与其无谓的争执,不如走上街头。
结语:
I march, therefore I am;
I protest, therefore I am.
这可能是这个城市市民和青年避免更大程度的“内爆”,找到自己存在,让自己可以生存下去的方式。
喝酒、抽烟、鸦片会让你开心,但不利于你的健康与发展,压抑的香港人选择的政治表达方式可以让香港社会找到短期的宣泄出口,但却会让全中国内地看到他们对内地的偏见,进而影响到香港的福祉与发展,最后反过来负面影响香港。这是香港人用短期的快乐换取长期的痛苦。也许,长期以往,香港人可以在两者之间(对大陆不友好,就不利于香港的繁荣,最终不利于自己)建立因果关系,汲取一些教训,但那又怎么样呢?他们的压抑和郁闷如何排解?
这是生活在水生火热的原教旨资本世界里的不幸的人们。这时应该可以回看百多年前马克思的论述。香港人希望找到的解决一切问题的处方(“真普选”),只是资产阶级提供的陷阱,让他们通过这样的资产阶级营造的上层建筑麻痹自己,并阻碍阶级意识和左翼政治的觉醒。香港大资产阶级及国际资产阶级(及其附庸的小资产阶级)所依赖的古典/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香港的维续,就在于为香港人灌输认同政治,突出族群政治,掩盖阶级矛盾。
香港“六七”对左翼政治的透支,冷战的结束导致的共产主义在西方主流政治话语中的终结,以及西方意识形态在当代对香港的垄断,使得香港已经被困在族群/认同政治之中,很难挣脱。而族群/认同政治又在快速拓展、下沉,全面的“社会化”,成为香港未来年轻人的最根本的政治,最根本的“存在”。资产阶级的“阴谋”在全面获胜。香港这一政治巨婴的政治觉醒真是遥不可及。
今天写到这里。希望能对内地和香港建制派的读者抛砖引玉,有所启发。